连载| 刘继明《人境》上部第十一章 -凯发官网k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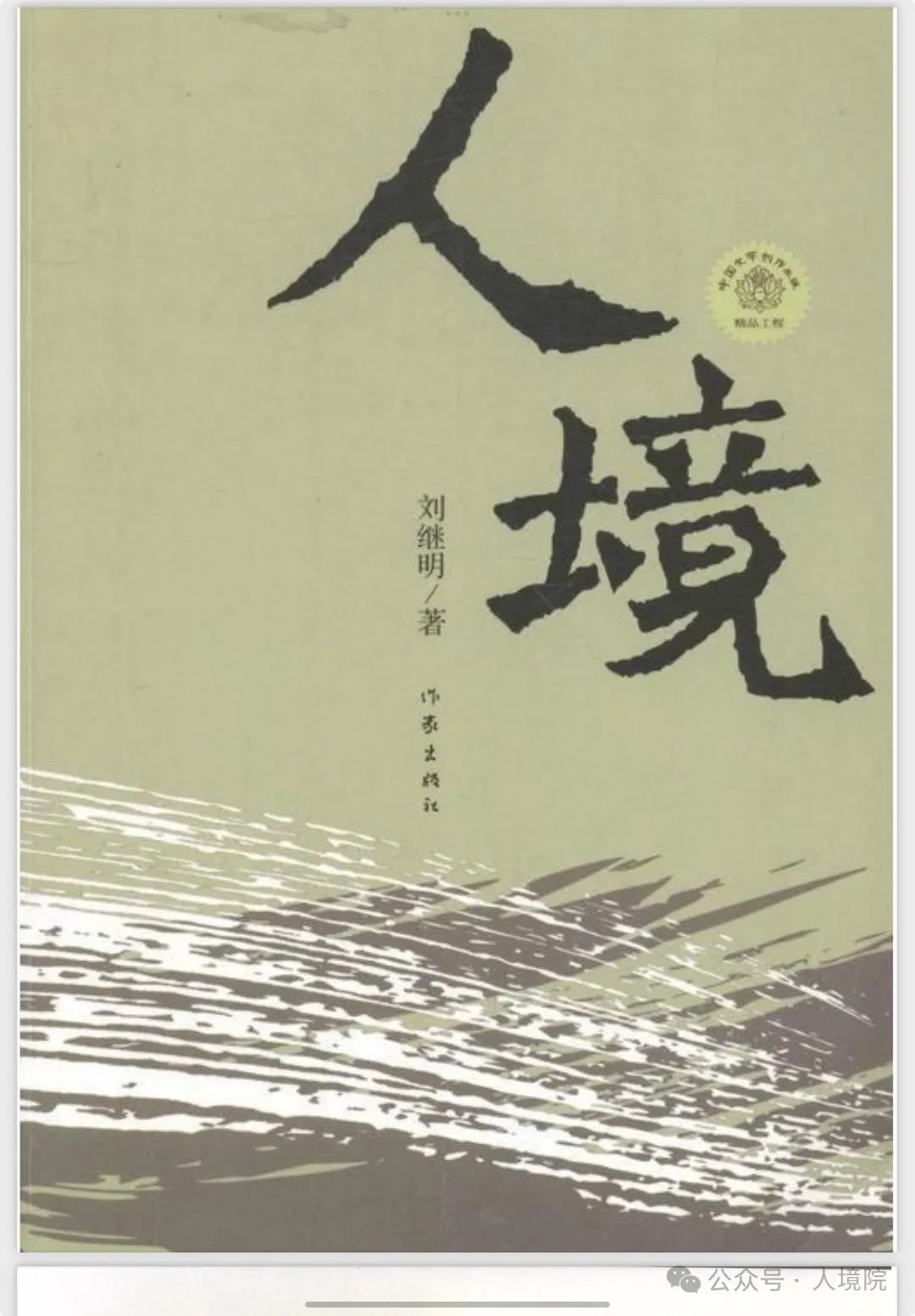
他得像一棵树那样,将双脚牢牢扎进土地,直到长成一片繁茂的树林。
翌年5月的一个早晨,马垃推开门,又浓又湿的雾像汹涌的海潮迎面扑来,他后退一步,愣怔了片刻,便扛着把铁锨,一头扎进了雾海。
雾是从半夜里开始下的,无声无息,铺天盖地,层层叠叠,粘粘稠稠,像牛奶,又像米汤,无边无际,海海漫漫的,整个世界都成了一个巨大的雾海。神皇洲只不过是这雾海中的一块小小的岛屿,村庄,田野,江堤,外滩,都淹没到茫茫的雾海里了。这是夏天的雾,她不像秋天的雾那样凝重沉郁,而有着丝绸一般的飘逸,云絮一般的轻盈;又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顽皮地在原野上奔跑撒欢,尽情地玩耍,她不时用柔软的小手触摸你一下的脸和头发,或扯一下你的衣襟,然后不等你反应过来,便一闪身子跑开了;你往前走,她也往前走,你往后退,她也往后退,始终同你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像在跟你捉迷藏似的。
马垃在大雾中走了一会儿,头发和眉毛上粘满了珍珠般的露水,一双塑料胶鞋也被潮湿的泥土弄得粘糊糊的,踩在地上发出呱唧呱唧的响声,他索性脱下鞋子,光脚踩着松软的泥土。雾的确太大了,三步之外不辨东西,所有的景物都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纱帐,变得影影绰绰,迷迷离离。耳边不时传来雾露凝聚成水滴,从草叶和树枝上滚落到地上的嘀哒声,此起彼伏,不绝如缕,似乎空气都变成了无数块湿漉漉的毛巾,用手轻轻一拧,便会下起毛毛细雨来。人走在中间,恍若走在笼子里,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甚至恐惧,担心自己永远走不出这无边无际的雾海,如果是一个孩子或对环境全然陌生的外地人,就更加担心自己在会大雾中迷路了。在外飘泊多年的马垃,真正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是不会迷路的,别说在漫天大雾中,就是被蒙上双眼,他也会毫厘不差地到达他要去的任何地方。马垃对此一点也不怀疑。比如眼下,他走在大雾弥天的外滩上,三步之外白雾茫茫,但他压根儿不担心自己走错方向。他对外滩的熟悉程度,似乎超过了自己的身体,他谙熟荒洲上的每一块水洼,每一棵杂树,每一丛芦苇,如同谙熟自己的每一寸肌肤。虽然过去才半年多的时间,但足以让马垃在这块被撂荒已久的土地上烧荒、耕种了。
现在,如果是空气澄明的白天,你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神皇洲江边的外滩上,一棵棵幼小的猕猴桃树随风摇曳。这些猕猴桃树才种下去不久,长得又细又瘦,被江面上刮来的劲风一吹就会东倒西歪,让人顿生一丝怜悯,没有一刻不让他牵肠挂肚的。在马垃眼里,这些猕猴桃树像一群稚嫩的孩子,做梦都盼望着它们早日长大,挂果。他每天都要来桃园里巡视几趟,给这棵树除草,给那棵树陪陪被田鼠刨松的土,还有施肥、打农药之类的活儿。他在劳改农场学到的猕猴桃栽培技术派上了大用场,平时总是随身带着一本果树栽培之类的书,一遇到技术上的难题,便拿著出翻一翻,然后对症下药……
当马垃在自己的猕猴桃园转了一圈回来时,太阳已冲破厚厚的大雾,露出了红彤彤的脸蛋。他走上江堤,抹了一把站在头发和睫毛上的露水,迎着万道霞光,放眼远眺,最先看见的就是他的家。
是的,马垃已经在神皇洲安家了。这个“家”,不是大碗伯的哨棚,而是他刚刚盖起来的房子。
一开始,大碗伯并不赞成他盖房子,哨棚那么多空房间,够他爷儿俩住的。但马垃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哨棚是供防汛时用的集体财产,自己总住在这里,未免有点沾“公家便宜”的嫌疑吧?再说,他不能老是被当成“客人”。多年在外的漂泊生活,使他讨厌“做客”的感觉。在内心深处,他早就把神皇洲当成了自己的故乡。自从三岁时跟着娘和哥哥一起流落到神皇洲后,他已经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了。娘葬在这儿,哥哥也葬在这儿。他们的生命已经化为阳光、空气和泥土,滋养着神皇洲的每一寸土地。只要想到这一点,马垃就会觉得浑身燥热,眼睛湿润,心也格外柔软,仿佛又重新变成了一个婴儿。这种隐秘的感情,他当然不能向大碗伯表达。这会让老人担心:在经历人生的大挫折之后,他的心智上是不是出了“毛病”?他只能说自己想单独“过日子”。对于他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了。就这样,大碗伯被他成功地说服了,并且主动帮他去找东生要宅基地。起先,东生找各种理由拖延,一会儿说没有闲置的空地,一会儿说虽然他承包了外滩的那些荒地,但户口不在村里,按规定是不能分宅基地的,等等。后来,他把一直放在原工作单位的城镇户口迁回了神皇洲,东生这才应允,但也有一个条件:不能占用耕地。最终,马垃得到了八分多田的一块宅基地,就在离哨棚不远的堤脚边,紧挨着一片水杉林。前面不远就是哥哥马坷和逯老师的坟地。由于地势低,已经很多年没人在上面种庄稼了。
去年过完春节,马垃就开始为自己的房子忙碌。他像鸟儿筑巢似地从河口镇上采购来了砖瓦、水泥、石灰,木料,以及那些零零碎碎而又是盖房子必不可少的小物件。这么多的建材堆放宅基地上,还得有人看守。于是,马垃在旁边用玉米秸秆搭了个棚子,白天打地基,晚上睡在棚子里,每天的饭都是大碗伯在哨棚里做好后给他送来吃的。乡下的小偷很厉害,大碗伯担心他夜里睡得太死,特意把“社员”留在他身边。没成想,“社员”还真立了一功:有天半夜,邻村一个农民偷了两包水泥正要开溜,“社员”突然从黑暗里扑出来,死死咬住了小偷的裤脚……当一切准备停当后,就正式开工了。除了瓦匠、木匠,小工都是村里请的。他把一张图纸交给主事的匠人,那是他熬了多少个夜晚才画出来的。不知是他画的不专业,还是过于复杂,年轻的木匠地理捧着图纸颠来倒去看了好一会玩儿,也没看出个门道来。没办法,他只好耐心地解释了一番,特别是房顶上的风车,更是费了他不少口舌。对方文化知识不赖,哦了一声:“马老师,你一定去过荷兰吧?”马垃摇了摇头,想说自己喜欢梵高的画作,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
当夏天的第一场豪雨落下来之前,马垃的房子盖上了最后一片瓦。房子竣工那天,他放了一挂十万响的电光鞭。鞭炮声响了半个多小时,把整个神皇洲都传遍了。
从外观上看,它既不像平原上到处可见、火柴盒那样千篇一律的水泥平顶楼房,也不像早年乡村常见的那种紫瓦屋。它的房顶尖而细,像一根竹笋,最奇怪的是房顶上耸立的那架风车,用桐油刷得黄橙橙的,每一片风扇足足有两米长,无风的日子,风车自然纹丝不动,风大时它就会转动,开始转得很慢,渐渐速度就快起来,而且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上了年纪的老人说,早年村里磨坊的水车转动时,也是这种声音。
猕猴桃园和这座房子,花掉了马垃的大部份积蓄。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从现在开始,他没有任何退路了。他得像一棵树那样,将双脚牢牢扎进土地,直到长成一片繁茂的树林。
此刻,马垃赤脚站在江堤上,一只手拎着被露水打湿的鞋子,一只手握着铁锨,整个身体侵染在色彩斑斓的霞光里,远远望去,像一棵燃烧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