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宋彬彬去世,卞仲耘之死的真相仍未大白于天下 -凯发官网k8
据红船融媒报道:“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于美国纽约时间9月16日逝世,享年77岁。”

2014年1月13日,新京报刊登报道:
“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此次“道歉”活动疑似由66届的刘进(北师大女附中在工作组派驻时期的“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的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省委书记,与宋彬彬等人同是高干子弟)和宋彬彬牵头组织,道歉的对象是“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其中受到伤害最大的,无疑是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长被批斗致死,副校长胡志涛受重伤,史称八五事件。
卞校长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也成了控诉那个年代和“毛主席晚年错误”的一大“罪证”。
然而,任何一起暴力事件,总该有一个清晰的调查结论。就该事件而言,究竟是谁人施暴,背后有无指使者,都应该成为调查结论的基本要素。吊诡的是,这些基本要素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
1969年12月,工宣队、军宣队驻师大女附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出的《对卞仲耘的审查结论》:“卞仲耘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1966年8月5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补偿。
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并为卞仲耘举行了追悼会。
1979年4月,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
2014年2月1日,内蒙古日报社旗下的正北方网报道:刘进和宋彬彬等人组织的“道歉”活动被新京报报道后,时年已93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指责宋彬彬等人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王晶垚是好样的,他拒绝以牺牲自己的妻子为代价配合那些人表演,以换取一些好处,敢于同话语霸权唱反调,精神可嘉。遗憾的是,王晶垚对历史、对事件的宏观认识显然有很大的问题。他在声明中非要强调“毛泽东为宋彬彬改名过程”,有意无意地将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尽管王晶垚在多个场合承认“八五”当天宋彬彬并未在场。
正是因为这样,更有必要厘清事件真相。尽管打死卞仲耘校长的“凶手”具体是哪些人,至今还没有清晰的结论,但大概对象基本是可以锁定的。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发出;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张贴了批判当权者的大字报;为了“控制”局面,六月初,刘少奇等人决定向各学校派驻工作组;6月3日,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
事实上,在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的三天前,宋彬彬等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已经成立。工作组进校成立了 “革命师生代表会”,由七人组成,宋为副主席之一。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批斗期间,卞仲耘已经遭受的殴打。
工作组的所作所为很快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七月底,工作组被撤销。
7月31日,师大女附中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的人员一时成了“保守派”。
工作组撤出后的八月初,尽管师生代表会的权力来源轰然倒台,使其“名分”不清,但“余威”犹存,事实上代替了前工作组成为“留守处”。八五悲剧就发生在这段权力更替的混乱期。
8月4日,师大女附中出现了干部子弟之前组建的老红卫兵组织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情况,她们强迫那些不幸的学生交代“反动思想”;同日下午,他们闯进几位校负责人办公室,对卞仲耘实施了殴打;8月5日下午,他们由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就在这场批斗中,卞仲耘拳脚乱棍交加致重伤昏迷。尽管学校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但担心施暴者“影响不好”拒绝将卞仲耘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导致卞仲耘含恨而终。
八五事件发生时,参与者基本都是干部子弟组织的红卫兵,反工作组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并没有参与,而且他们始终是少数派,从未在学校掌过权。
在报道“道歉活动”的当天(2014年1月13日),新京报还刊登了刘进的文章《为贴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道歉》,刘进在文章中也承认:“卞校长死于校园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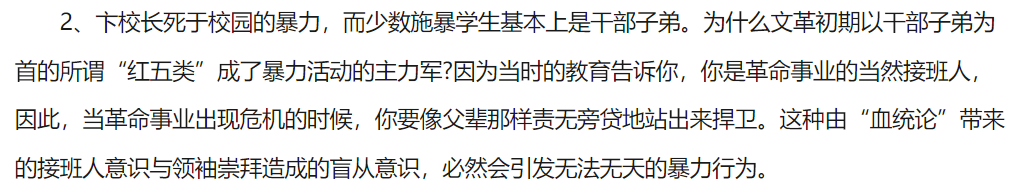
从这个表述看,刘进想必是知道行凶者具体是哪些“干部子弟”的。遗憾的是,他并未指明,相反他在这篇文章中还摘清了自己和宋彬彬的直接责任,只检讨了自己和宋彬彬的“领导失职”。
“干部子弟”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恐怕与他们的父母脱不开干系。
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按我们的理解,“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进行,准备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组织一些批判,最后处理一些人……在群众分裂成不同的派以后,我又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这个“当时按我们的理解”,显然严重偏离了毛主席发动运动的初衷,严重干扰了斗争大方向。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主席认为: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
综上,卞仲耘校长之死,显然是某些“干部子弟”为了“保护”父母、干扰斗争大方向,故意制造混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造成的悲剧。这笔帐又怎么能算到毛主席头上呢?
至于所谓“毛泽东为宋彬彬改名”是发生在818接见之后,而卞仲耘校长却是死于半个月前,跟“改名”没有丝毫关系。
况且接见的时候,毛主席也并没有要给宋彬彬改名,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不过是她自己的行为;毛主席的“武”也只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武”,从来没有支持过“武斗”。不仅没有支持过,毛主席还一直在制止武斗,一再强调“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1966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