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下降,基层产科静悄悄 -凯发官网k8

过去一年多来,各地医院的产科陆续传出被关停或合并的消息。与之对应的是,2023年国内出生人口902万,和2016年放开二胎后的生育高峰相比,产科分娩量少了八百多万。
2月28日,知名妇产科专家段涛公开呼吁,「救救产科!你们担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担心的是产科学科的塌方。」一时间,网友开始辩论起到底是产科,还是重压下的年轻人更需要被拯救?
喧嚣声中,作为一个最早感知到出生率变化的行业,有一批人已经被轻轻拨转了方向。
文|李晓芳
编辑|王珊瑚
基层产科静悄悄
事情发生前总有预兆,王晴早有察觉,也做了一定心理准备。但春节后返岗,听到科室主任宣布,医院产科即将停止服务,那一瞬间,她还是觉得,「非常受不了」。
王晴27岁,是某一线城市一家二级综合性医院的产科护士,已经工作了8年。消息公布后,同事们起初还开玩笑,「我们医院的出生证明以后都是限量版了。」但很快,孕妇建档工作停止,之前订购的、药厂还没来得及发货的产科用药都陆续退了,再后来,护士长说剖宫产包,还有其他无菌包都不用再消毒了。王晴意识到,「我真的见证了(我们医院)产科即将落幕的历史时刻。」
幕布当然不是在瞬间落下的。大约是一年多前,产科的工作已经很不饱和,她开始兼任部分内科的工作,给老人拿降压药、输液。2023年的最后几个月,产科每月的接生数量跌至个位数,到今年2月,产科宣布关闭前,「我们只接生了一个,然后就没有了。」
在广西东南部某乡镇卫生院,助产士梁丽娜「今年还没有开张」。过去15年,她一直在这里的产科工作,同时管理医院的接生登记本。她清晰地看到登记本上的名单越缩越短,「以前每个月最低都能有30多个产妇,能保证至少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生儿。」后来这个频率变成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
如今妇产科唯一还算热闹的时段是早上,偶尔有人来做检查,「到下午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过来了,整个医院都是静悄悄的。」
临近几个乡镇医院的情况也算不上好。医护人员有时在一起开会,交换各自的信息,梁丽娜知道隔壁市另一个镇上的卫生院前两年已经停止接生工作,只保留了妇科和孕检。还有相邻的一个镇卫生院,因为配备了麻醉师,能开展剖腹产手术,周围几个镇上的居民都愿意过去生产,「最高峰一个月都有一百多个,去年开始直接跌到一个月三四十,今年到目前才十个左右。」
梁丽娜工作的卫生院不大,只分三个科室,综合科、妇产科和中医科。她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妇产科就要和中医科合并了,「还没有正式通知,不过我们主任都在讨论了,也没有必要单独保留产科。」
过去几年,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多个医院的产科重复上演。《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1年,国内妇产(科)医院数量减少了16家。2023年9月以来,公开宣布暂停或合并产科业务的医院数量,至少有9家。
这些医疗机构绝大部分是二级综合性医院和一级基层医院、卫生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说,在出生率不断下跌的情况下,目前最受影响的也确实是一二级医院,「三甲医院毕竟有好的医生资源,还是能吸引大多数病人。」
即便是三级头部医院,依旧能感受到危机。段涛说,2016年二胎刚开放时,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全年分娩量达3.4万。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被称为上海的「大摇篮」,分娩量连续8年位居上海第一,「现在一年差不多2万5(例),上海过去一年新生人口20万,现在连10万不到,我们这个分娩量已经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我们下降这一点,其他医院受影响的肯定会更大。」
前段时间,段涛和浦东新区的产科主任开会,大家的讨论重点是「产科转型」。他记得一位有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产科主任发言,说自己所在的综合性医院要重新装修,一向不满意产科的院长趁机关闭了整个科室。那位主任哽咽了。段涛也很无奈,「他们干这一行干了十几年,花了多少时间精力,转行又转去哪呢?」
开完会没多久,段涛写下了那篇「救救产科」的长文:「如果再不改变现状……产科整个学科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塌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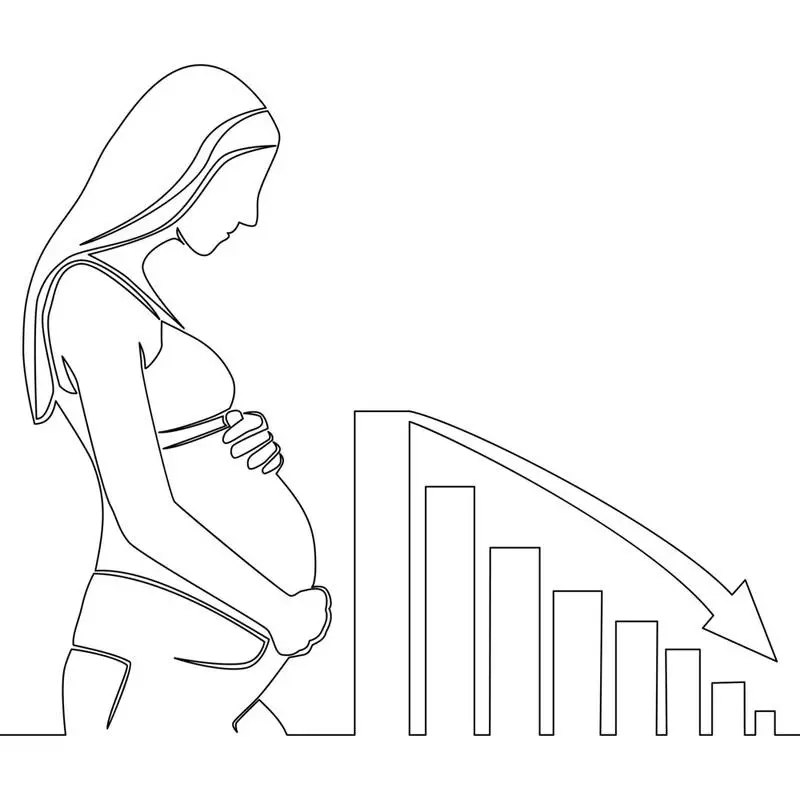
从高峰滑落
段涛还记得产科巅峰的时期。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开放,那年全国新生人口1786万。段涛所在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有90多名产科医生,一天得接生近100个孩子,还得查房、写报告、病历。当时医院里有个说法叫「闭经指数」,指的是年轻医生在各科间轮岗,每次轮到产科,忙得月经都不来了,到了妇科又好了。
在另一座一线城市,产科护士王晴毕业时正好是2016年,和其他医护一样,她印象最深的是产科的楼道,「因为生孩子的太多了,楼道里都塞满了病床。」每天夜班更是像打仗一样,「我们科有两个产床,经常是我们在里边接生,待产室里还躺着好几个已经阵痛、准备生产的孕妇,一晚上可能就要出来五六个孩子。」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不少数据机构预测,和过去相比,开放后第一年新增的出生人口至少超过200万,且未来几年出生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
2016年最终只比2015年增加了131万新生人口。但那时大部分医院产科床位已经处于紧缺状态,为了迎接全面二胎,解决「建档难」和「一床难求」的问题,2016年下半年,原国家卫计委要求,在县级医院新增产科床位8.9万张,三级医院可以将特需病房调整成普通病房增加床位,同时争取在「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2016年10月29日,在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家长们推着婴儿车排起长队,等候护士给新生儿做护理。
高峰没能持续太久。「2017年开始,每年的分娩量都在下降,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变化,」段涛说,「但影响是有延迟效应的,下降到一定程度,去年就900多万,后续的负面效应都集中凸显出来了。」
王晴和梁丽娜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所在医院的分娩量从2017年底开始有下滑趋势,当时主要因为原国家卫计委从2017年7月开始,陆续在各个城市推行《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规范》。
二胎开放后,多家医院反馈,高龄产妇比例上升至20%,而过去这一数据在10%左右。《工作规范》按风险严重程度,由低到高以「绿、黄、橙、红、紫」5种颜色对孕妇进行分级。王晴说,她所在的二级医院之后都不能接诊橙色级别以上的孕妇,「当时就分流了一波人。」
致命一击来自出生率的持续下降。梁丽娜回忆,大约从2021年开始,她所在的乡镇医院肉眼可见地空了。这一年国家开放三胎,但新增人口从2020年的1200万,跌至1062万。梁丽娜所在的乡镇离市区大约十几公里,不算远,且交通发达,产科床位不那么紧张后,很多人会选择开车到十几公里的市区生孩子,「求的就是一个安全。」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李岩2022年曾经到湖北省两个乡镇卫生院进行调研。据他统计,一个乡镇一年仅有200左右新生儿,「新生儿的数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产科的发展空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乡镇卫生院妇产科变得静悄悄是资源集中与利用的表现,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下的优胜劣汰,在全国普遍低生育、人口仍然向城市集中的背景下,需要对乡镇、村庄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
但他也写道,「资源整合或者被砍掉之后应该怎么办?没有补充力量进入,农村女性想要看妇科病、想要做产科手术只能去县城,结果是『看病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这与我国长期坚持的医改方向与目标是相矛盾的。」
段涛也提出,「中国人口的出生数量有一半以上是在县级及以下医院的,产科的就医半径还比较短,不像看肿瘤做试管婴儿,可以全国跑。特别是孕程后期,她们每一到两周就要做产检,你不能让全县城的孕妇都从乡镇跑到县里生孩子,医疗的可及性就没了。」
「产科以前那么忙是不正常的,产妇都睡走廊了。」但如今时不时传来的关停消息,同样让段涛感到忧心。

2017年8月5日,一名小女孩和她即将生二胎的妈妈。
被「嫌弃」的产科
梁丽娜从去年开始就没有领过绩效了。身边很多同事都在考虑下班后做点副业。「有同事出去摆摊卖东西,我们很多护士就找点手工活,弄一些塑料珠花,能在家里做,每个月多几百块钱。」
她也问过家楼下制衣厂的老板,自己能不能干一份兼职,但被拒绝了。老板担心她在医院经常值夜班,遇上工厂赶货,也抽不出时间来帮忙。
过去生孩子的人多,医护人员能拿到的绩效也高,当时梁丽娜一个月工资能有6000多元,在乡镇是个不错的水平。她有编制,现在每个月工资还能维持在3000元左右,但「我们医院的合同工每个月才1500,还要租房、吃饭,他们也觉得做得没有什么意义。」
过去半年,她所在的产科已经有三位医护人员离职。
在她的观察里,妇产科一向不是医院的发展重点。她所在的乡镇级别医院自然分娩的医疗费是230元,「我们一个产包进货价是九十块钱,包括棉签、一次性垫布之类的,还有一个接生包,就是产钳、剪刀,用一次折旧价算几十块钱,再加上人工,就剩100块钱。」加上整个孕期要收取的各类产检费用,梁丽娜说,医院接待一个孕妇,大概盈利1000多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产科教授李小毛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如果产科月分娩量无法达到50个,就难以覆盖整个科室正常的运营成本。超过100个,科室的运作才处于良好状态。
出生率下降后,产科的运营压力首先暴露出来。段涛说,在所有科室里,产科收费是偏低的,顺产费用通常是几百到一千元,剖宫产稍高,能达到两三千元。「但维持产科的成本又是很高的,其他科室晚上可以少点人,产科24小时都要有人,很多产妇都是晚上发动,产房医生、麻醉医生、助产士、护士,一天三班倒,最起码得有几十号人。」
而对于三级医院来说,还有另一重压力。2019年,国家卫健委启动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鼓励大医院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指标是cmi指数(医院收治病例的疑难危重度),和四级手术(最高级别)。
段涛认为矛盾的地方在于,产科的原则是保障母婴安全,把母婴并发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所以产科做得好的时候更多的是顺产,预防工作做好了,就没有各种并发症,cmi指数很低很低,更不要提四级手术。要医院指标好看,那遭殃的就是产妇。」
段涛感叹,「医学的学科不像养猪,你能在一个比较短的周期很快做决定,成本不需要那么高。但你要培养一个好的医生要花多少年?十几年吧。现在出生率又越来越低,产科不挣钱,能获得的投入会越来越少,医生的机会也少,没有人愿意做产科,以后产妇有个突发情况,谁去做手术?」
他担心未来有一天,产科也会重复儿科那样的命运。「少子化这是个大趋势,但如果什么都不做,产科可能就直接自由落体往坑里掉了。」
3月2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其中还提到,要努力使综合性医院产科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平均水平,严禁向产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
在段涛看来,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真正的落地,医院每天都要算账的,政策到了下面能落实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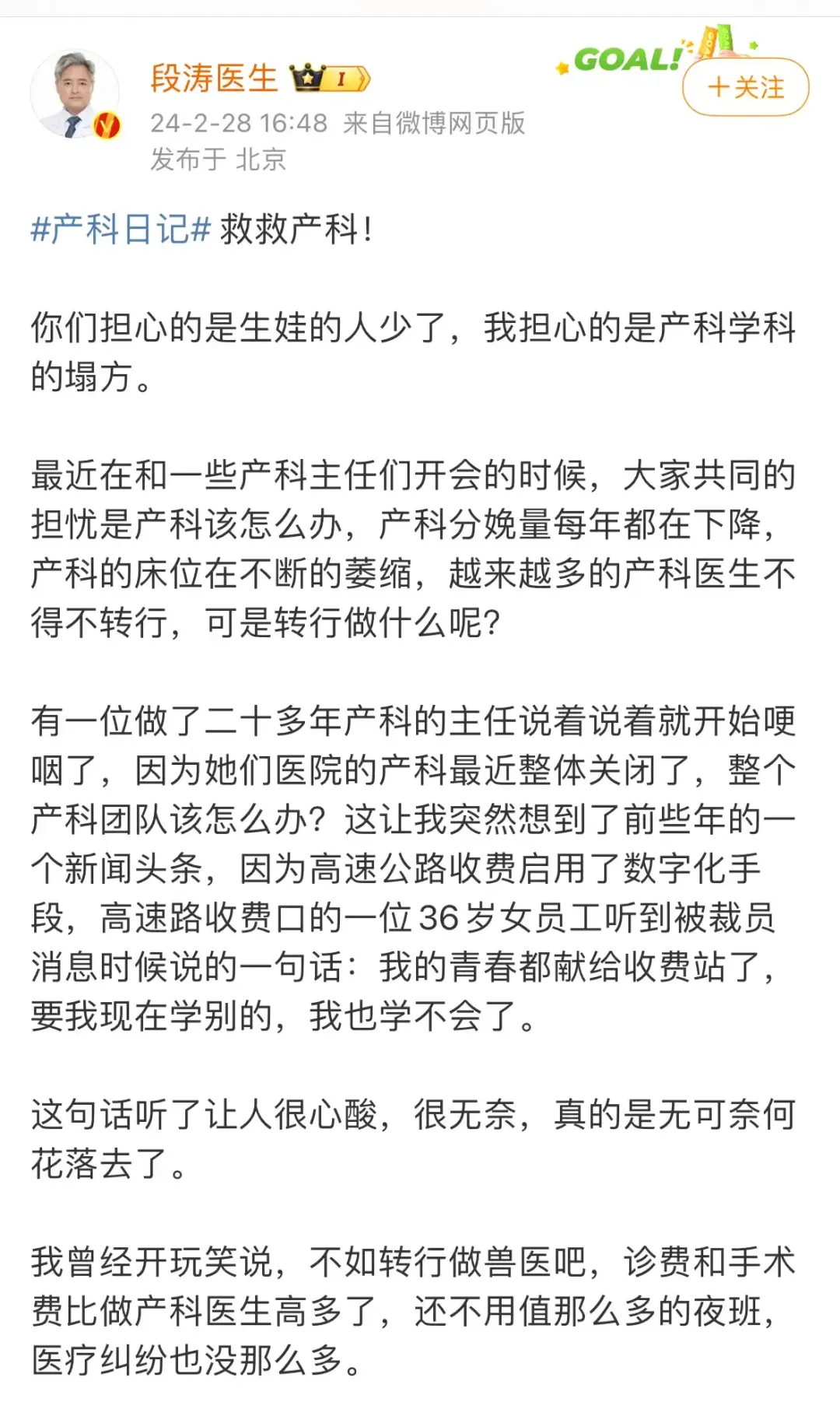
段涛的微博图片来源网络
另寻出路
王晴如今大部分时候都在内科工作,一个月前,医院已经正式发出公告,「停止助产技术服务与产前筛查技术服务项目」,之前已经建档的产妇将陆续分流到周边其他医院。王晴说,后续医院应该就要处理婴儿床、改造病房,产科的帷幕要彻底落下了。
内科的工作很饱和,病人从来没有断过,她发现许多老人用不了两三个月,还会再来住院,「人多了都住不上。」看起来,她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失业危机了,毕竟人们可以不生育,却无法避免衰老。但也说不好,她犹豫了下,8年前她刚进入产科时,也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失业,「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每个人都会面临生孩子这个问题。」
她感慨,「以前做产科,现在干内科,这不就是一个从新生走向死亡的过程吗?」唯一值得高兴的是,她的收入可以涨回来了,去年分娩量最低的时候,她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
梁丽娜能理解如今年轻人不愿生育的想法。她36岁,有两个孩子,婆婆有时还会催她再生一个。她说如果三胎开放时间早六七年,自己肯定考虑生,「那时候才三十出头,家里也还有点积蓄,父母也不算很老。」但现在经济压力大,养两个孩子已经很累,「折腾不起,打死都不会生。」
梁丽娜喜欢助产士这份工作,「我想着可以干一辈子,而且看着新生儿出生,感觉真的是挺伟大的。」每次婴儿哇一声哭出来,就是梁丽娜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她叹气,「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妇产科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的。」

2024年2月10日,浙江省舟山医院产科分娩室迎来龙年第一个「龙宝宝」出生。图为一名医务人员正在为「龙宝宝」敲脚印。
一些年轻的医学生在挣扎。浙江某医学院,一位妇产科专硕研究生入学时就规划好,毕业后就回家乡镇上的医院当一名产科医生,压力不大又安稳。然而两年后,2023年6月,父母告诉她,镇上卫生院的产科被取消了。
内蒙古一位助产专业的学生说,刚上大学时,所有人都跟她强调助产士稀缺,她因此放弃转换到检验专业,如今即将毕业,「结果我现在找不到工作。」今年3月,教育部将护理学、助产学调整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等特殊专业,被列入国控专业的通常是市场需求量已经饱和的专业。
31岁的赵慧子郁闷了好一段时间,她在某二线城市的医科大学读产科博士。2023下半年开始,她发现学校附属医院的产科病人越来越少,病床经常住不满。但年初她决定读博时,产科的情况还不是这样的,「没想到之后我可能要失业了。」
赵慧子最近在搜集一些大型医院的产科招聘信息,希望尽早做好准备,「从招聘人数上看,这几年一直是缩减的。我家乡有些医院,以前可能一年招两三个,现在基本都不会招了,对学历的要求也高了,以前本科生就可以,现在要研究生博士。」
她承认自己有些迷茫,就像乘坐的邮轮已经开到了大海中央,没办法中途跳下去了。她只能鼓励自己积极起来,「我读博也还有机会转成科研岗,还有一些师兄去到专科院校当老师,还有医药生物公司,医学翻译。」她把可能性一一列出来。
最后,她只能安慰自己,「我们学校还不错,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都还找到了工作,应该不会那么糟糕。」
(除段涛外,文中其余人物为化名)